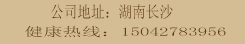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大便失禁怎么回事 > 后颅窝大便失禁 > 巫山县年禁毒征文获奖作品子午卯酉
当前位置: 大便失禁怎么回事 > 后颅窝大便失禁 > 巫山县年禁毒征文获奖作品子午卯酉

![]() 当前位置: 大便失禁怎么回事 > 后颅窝大便失禁 > 巫山县年禁毒征文获奖作品子午卯酉
当前位置: 大便失禁怎么回事 > 后颅窝大便失禁 > 巫山县年禁毒征文获奖作品子午卯酉
巫山县文联、作协出品
子午卯酉
梁长燚当穿着夹克的一男一女走进院子的时候,秀儿正埋着头在院坝边的洗衣台上搓洗衣服。
这洗衣台是勇哥出门前才为她搭建好的。有了这洗衣台,她就不用勾着腰在木盆里洗衣服,也就不会腰酸背痛了。
所以,一边洗衣服一边想着勇哥的秀儿是幸福的,极其的幸福。虽然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嫁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但她的男人对她是好的。
当然,严格意义来说,用“嫁”来表述她和勇哥的婚姻还是有些勉强。他们有结婚证,是合法的夫妻,但没有嫁娶,没有婚礼,连一个简单的婚礼都没有。甚至,连秀儿的父母都没来这个地方看过。
秀儿和勇哥是在东莞打工时认识的,然后情不自禁的走到了一起,并且有了一个小孩。有了小孩之后,他们起初也没有打算回这个地方来。但是,勇哥的父亲病重之后,他们不得不回来。
山茶花坪是一个好地方。当然,他也是有缺点的,但最主要的缺点还是落后、贫穷。
起初,秀儿对这里的生活极为不习惯。时间一长,她就适应了许多。当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变,勇哥挣钱为家里苋上了自来水,把出门的路扩到了两三尺宽……唯一不足的是,勇哥隔三差五就要出门,让秀儿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公公和孩子。
“你是张秀吧?!”穿夹克的女人像是在询问,也似乎只是在打招呼。
听到有人说话,秀儿立即转过身,冲了冲手上的泡沬,从屋里搬出椅子给客人坐。在山茶花坪,特别是在位于山茶花坪最东端、三面临崖的这个家,一年半载是难得见到一个人影的。
接过夹克女人递给她的那张盖有鲜红大印的拘捕通知书后,秀儿的脑袋立刻炸裂,犹如盘古开天辟时的巨大浑浊,继而又是群魔乱舞,天地间只剩下狂风大作卷起的石走沙飞。
“不会的……勇哥不会的……他怎么可能走私毒品……他只是一个长途货车的押货员……”
望着夹克男女消失在山路尽头的灌木丛,秀儿才想着摸索着坐下。可是,她的手,她的身体完全不听她的使唤,天空、大地仍在极速旋转。她运足全身的力气使自己镇定,然后迅速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得先坐下。当然,就是她不打算坐下,她也没有力气继续站立。
听到院子里发出的沉闷声响,勇哥的父亲咧了咧嘴,艰难的开始向院子里喊话。他使出了浑身的劲,可呼唤的声音仅有他自己能够听到。严格意义来说,那只能算是嘟哝,因为他的喉管根本没有发出什么实际和明确的声响。
秀儿的孩子正在爷爷的轮椅旁边起劲儿的踩橡皮鸭。每当橡皮鸭随着他的小脚抬起而发出吱吱声响的时候,他就乐呵呵的望着爷爷,期待爷爷给予他一个鼓励。可是,坐在轮椅上的爷爷已经无法给他表扬,甚至一个微笑。
终于,秀儿得以醒来。她到底是怎么醒来的?是因为后背透心冰凉,还是因为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喊?秀儿记不得了,也没有精力来想这个事情。她坐在地上,把孩子拉过来一把抱在怀里。
天空漆黑一片,秀儿看不见孩子脸上的鼻涕,也不见自己身上的泥土。待孩子的哭声平息了下来,她才缓缓起身,把屁股挪到木椅子上。
秀儿开始努力搜寻关于这个下午的记忆,可这个下午的时间被拉得很长,长得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她一直认为和她和勇哥是亡命之交,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美好时光、争吵赌气,在时光的沉淀中积蓄丰满了他们的爱情。可这个下午,让这一切都如过往云烟,轻的不值一提。
洗衣台上的衣服还泡在水里,似乎是很久很久泡在那儿的。秀儿第一次体会到“恍若隔世”这个词的含义。
屋里漆黑一片,秀儿抱着孩子进了屋开了灯。
勇哥的父亲两眼直盯盯的望着秀儿。他虽然不能说话,但脑子还能使,他极其希望知道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爹,我老毛病患了。洗着洗着衣服就晕过去了。”秀儿找了一个理由,就把孩子放在爷爷的轮椅旁边,进厨房开始做晚饭。
勇哥的父亲不能说话,用力朝鸡圈努了努嘴。秀儿知道,他是让自己宰一只黑母鸡炖了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山茶花坪的人都信黑母鸡炖的汤可以治晕病这个偏方。当然,在那些物资匮乏的日子,别管黑鸡白鸡,还是母鸡公鸡,能够吃一些鸡肉喝一碗鸡汤总是能够滋补一下身体的。
虽然,勇哥的父亲对勇哥被抓的消息一无所知,但这件事在村寨里早已是妇孺皆知。
当得知勇哥永远不可能从牢里活着走出来的时候,村里那些有家室、没家室的男人都对秀儿投以无以复加的怜爱,有的更是明目张胆的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
秀儿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现在,她就是一个名义上还有男人,一个不是寡妇的寡妇。她毫不客气的拒绝了所有或明或暗的帮助、善意或者不怀好意的关心。
勇哥不可能再往家里捎钱,可家里的开支一样没少,爹的药、孩子的面包、平娃的学费。平娃是勇哥的弟弟,正在读高二,每周都会回来一次。他每次回来,都要带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走,雷打不动。
镇上、县城也是可以找工作的,可她出去上班之后,爹就没有人照顾。
秀儿可以拒绝所有人的帮助,但绝不可以拒绝妇女主任的帮助,因为妇女主任也是女的,她对自己不可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再说,妇女主任还承诺,她上班的时候,她可以帮她照顾她爹。所以,当妇女主任帮她在镇上找了一个服装店的工作后,她毫不犹豫的就去了。
镇上的居民不多,到了下午,店里就没什么客人。秀儿跟老板商量,看能不能四点钟或者五点钟下班。这样,她可以早点回家给爹做饭。老板想想也对,就同意了她的要求,不过每个月的工资少了块钱。
虽然少了块钱的工资,秀儿还是非常满足,毕竟最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
对于未来,她又充满期待,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这并非是因为秀儿的乐观,而是她的生活已经跌入了最低的低谷,没有再差下去的机会。不过,当她提着两斤五花新鲜肉进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想法太过于天真,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奢望,目前的生活真还不是最糟糕的——刺鼻的大便味一股脑儿窜出来,勇哥的爹大小便失禁了。
“秀儿,你带着娃儿走吧!你走了,勇哥他爹,还有他弟,村里给他们申请低保户、贫困户,再把他爹送到敬老院住,那儿有专门的护工。”给爹收拾好,秀儿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一宿,还是不打算接受妇女主任的建议,决定留下。
马姐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近秀儿的。她隔三差五就会到秀儿的店里坐一阵,天南地北瞎侃一番,走的时候顺便在墙上选一两件衣服带走。不知道为什么,马姐每次随意取的衣服都是店里最贵的衣服,而且从来不讲价。秀儿有些愧疚,好像她故意卖贵货给马姐一样。为此,她多么希望马姐能挑一两件便宜一点的衣服。但是,事与愿违,马姐从来没有挑过便宜货。后来,秀儿甚至想,如果这店是自己的,她宁愿亏本也要给马姐便宜两次。
秀儿对马姐的所有好感在一次看似随意的聊天中戛然而止。其实,这远远不是好感的终止,而是反向变为憎恶,深深的憎恶。马姐竟然说,可以带她去县城的洗脚城上班,一晚上就可以挣两三百块钱。
秀儿很好奇,什么工作可以这么挣钱?就是有这么好的工作,她秀儿何德何能何以胜任?
“亏你还是当妈的人咯?这就不懂?不就上个床吗?和那些狗男人睡一晚,身上又不少一块肉?你和你家勇哥睡了这些年,你损失了啥?”
秀儿内心一颤。她从来没有在店里与人提起过家里的事情,特别是勇哥这糟心的事。看样子,马姐对自己是蓄谋已久。
秀儿的态度十分坚决。
离开服装店的时候,马姐习惯性的还是挑了件衣服,一件纯白的吊带,不过价格极为便宜。看样子,她确是识货的。
“都人老珠黄了,还穿这么素静的颜色,不害躁。”看着马姐离去,小珠不服气的撇了撇嘴。
小珠也是外地人,据说是为了爱情到这个地方来的。情郎一直没有现身,她就找了一个理发店当学徒。理发店就在服装店的斜对面,没事儿时,她就爱跑到服装店和秀儿唠嗑。
“你说,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吗?”小珠总会问秀儿这个问题。
“也许有吧!”要是在以前,秀儿会毫不犹豫的给小珠肯定的回答。但现在,她伤痕累累,已经没有勇气来回答,甚至思考这个问题。
看小珠不说话,秀儿补充说:“爱情,就是你宁愿死去也要和他在一起。不管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有人为你,或者为了你爱的人而疯狂一回,人生就当无悔。”
说了会儿话,秀儿把给孩子买的一些零食拿出来给小珠吃。小珠知道,秀儿挣的钱不允许自己大朵快颐,她只是象征性的吃了那么一点点。
过了几日,天空下着雨,服装店里没有一个人。秀儿与整个世界被厚厚的雨帘隔断开来。
“我给你尝尝好吃的。”小珠没有打伞,径直穿过雨帘跑过来。
“啥好东西?”
“尝尝就知道了。这东西超提神的。”说着,小珠掏出一张锡箔纸,在上面撒了一撮白色的粉末。
“你这玩过家家呀?”秀儿忍不住笑出了声。她突然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大伙儿吃方便面的调料就是这样吃的。谁买了一包方便面,就会把调料包打开,给要好的同学每个人手掌心倒一点。然后,大家扬起头将其倒在嘴里,最后还要忍不住用舌头把手掌心舔干净,也不管手脏不脏。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们手上不可能有片刻的干净过。
小珠摁动打火机,一股青色的烟雾轻轻飘了上来。
“这是个什么吃法?”
小珠也不答话,一边把鼻子凑上去吮吸,一边朝秀儿招手。
秀儿疑惑着也探过头,轻轻地试着吮吸了一下。
“好香啊?这是什么东西?”
待锡箔纸上的粉末燃尽,小珠才答话:“别管是什么?味道怎样?”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美着呢!”
“你知道吗?这东西不光是好闻,关键是还能提神。”
小珠说的不错,这东西极能提神。回到山茶花坪,她为勇哥的爹全身上下清洗了一边,又给孩子洗了一个澡,然后把屋里需要洗的衣服全部找出来洗了一遍也不乏,就像有使不完的劲。
连续几日和小珠一起分享了这神秘的美味之后,秀儿精神状态一直极好。但她不可能一直吃别人的,就向小珠打听这白色的调料包从哪里买的。
“我请你吃调料包,你请我吃旺仔小馒头。”小珠笑了笑,就是不告诉她这东西在哪里买。
星期二,小珠没有来服装店。这是少有的事。
第二天,星期三,小珠还是没有来服装店。
保持了十多天亢奋的秀儿突然像霜打的茄子,萎靡不振,口干舌燥。勇哥出事后,她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一个下午,醒来后就迅速恢复了理智,虽然情绪低落,但日子总归一步一步的往前过。现在,秀儿的突然消失竟让她肝胆俱裂。
“不应该呀!不应该呀!”秀儿一边情不自禁的往理发店走一边想,难道自己是同性恋?难道真的是同性恋?或者说是双性恋?对呀,自己以前只为勇哥这样魂不守舍过。不对,我虽然和小珠确实要好,但只是玩伴,我想的只是她的调料包。
理发店本来就很小,里面就一个人在烫头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许久没有到服装店来过的马姐。
马姐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秀儿啊,你也来打理头发呀?”
秀儿想,马姐虽是个婊子,但终归是个好人。要不是她一脸热忱,自己该有多尴尬。“我几天没有看见小珠了,来看看她在忙啥呢?”
“鬼知道她去了哪里,昨天早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起床后一句话没说就上中巴车进城去了。像我欠她钱似的。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的,她在这里当学徒,我不收师傅钱,她也不要工资。明明是说好了的嘛。哎,现在这些年轻人呀。”理发店的老板一边给马姐打理头发,一边唠唠叨叨。
马姐除了思想龌龊,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能干的人,似乎手眼通天,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她竟然知道小珠在县城的住处。
到了城里,马姐原本弥勒佛祖式的微笑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个光着膀子、纹着水蛇的黄毛递给秀儿一个白纸包。“你找的是这个吧!”
秀儿点了点头。
“你要多少?”
“给我二十块钱的吧!”
黄毛笑了笑,从钥匙串上取下挖耳勺,舀了两勺递给秀儿。
“你这东西叫啥?怎么这么贵?”秀儿想,这肯定是马姐在报复自己。毕竟,她在自己的店里买了那么多衣服,却没有将自己拉下水。今天吃点哑巴亏,把这东西叫什么名字搞清楚,以后在其他地方还是可以买到的。这样想着,她掏出身上的所有钱,留了三十块钱的车费,然后全部放到了桌子上。
“姑娘挺大方的嘛!”说着,黄毛把纸包递给秀儿,还送了她几张锡箔纸。
“你这东西叫啥名字来着?”
黄毛怒了她一眼,不做声。马姐接过话,淡淡的说了句:“海洛因。”
正如马姐所预料的那样,秀儿不可能到其他地方买到海洛因。
每次从马姐待的洗脚城出来,秀儿就发誓再也不来了。可过不了多久,她依然又出现在这里。后来,她干脆就留在这里,因为服装店的那点工资完全不足以支付她购买海洛因的钱。她理所当然的开始陪不同的男人睡觉,然后用换来的钱换海洛因。
在洗脚城,秀儿像干以前干过的所有工作一样,绝不敷衍。因此,她的客人异常稳定,且出现缓慢的增长势头。客人增多了,她的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要不是检出艾滋病,或许她的生活就这样赖着过下去。至少,秀儿是这样想的。
马姐把秀儿送到村口,就开始折返。
因为早上和洗脚城的姊妹们一起吸过,秀儿现在对海洛因并没有什么需求。但是,她现在得去妇女主任家接孩子,她必须得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因为这个理由,她在路边的一块青石板上坐下,从包里掏出一撮海洛因精心堆砌在青石板上,然后点上。
看着那一缕淡淡的青烟妖娆起舞,秀儿恍恍惚惚,不知所以。她第一次来山茶花坪的时候,勇哥也和她在这块青石板上坐过,而且坐了许久。她清晰记得,勇哥蹲在自己的面前,一脸诚恳地说:“我家里很穷,你要有心理准备。”秀儿满不在乎昂着头:“我老大远跟你来,也不是为了嫁豪门的。”“你放心,我家虽然现在穷,但一定会发达的。我爹建房子的时候,专门请地脉先生看了子午卯酉,说是大吉的方位。你看,这才几年,我就抱得美人归咯。”对于子午卯酉是个什么方位,秀儿不得而知,但现在看来,这个方位并不怎么样。别说大吉,简直就是大凶。秀儿想,待在监狱里的勇哥现在肯定也会懊悔他曾经吹下的牛。不对,不是懊悔他吹下的牛,应该是懊悔他曾经的判断和自信。在秀儿胡思乱想的当口,那一撮海洛因几乎就要燃尽,她迅速扑上去,张开嘴,从顶端把整缕跳跃的青烟吸了进去。
呆在山茶花坪的秀儿再也不洗衣服,也不打扫房间,只是每天坚持为爹和孩子做三顿饭。虽然饭点不准,但还是可以确保一家人不饿肚子。
每个星期,她都会去一趟县城,去洗脚城弄一些海洛因回来。很快,她在洗脚城存下的万多块钱就见了底。她试着向黄毛、马姐赊购海洛因,但被果断拒绝。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秀儿赌气的第一次空手而归。但是,没等回到山茶花坪,还只在大巴车上,她就全身抽搐,倒在车厢里一阵翻滚。驾驶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迅速把她送到沿途的一个乡镇卫生院。
从医院出来,秀儿知道,这样的日子将是她的常态。躺在一块雪白的芦苇荡里,望着陌生的天空,一滴,或者两滴眼泪从她的眼眶滑落了出来。这是秀儿好久没有过的清醒。
在洗脚城,她骄傲的递了两百块钱给黄毛,取了一些海洛因。然后又在城里逛了一圈,买了一些孩子极其喜欢的糖食、勇哥爹喜欢的酱肉包以及鼠药。本来,她打算给自己买一条裙子的。现在,任何一条裙子穿在她的身上都不会显得臃肿。实际上,她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在镇上,她又拐弯去敬老院看了一眼,里面的老人生活的干干净净,房间里有电视,还有专门的护工。如果她当初按照妇女主任的建议,自己带着孩子离去,老人在这里生活是不是更惬意?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不去假设没有发生的事情。
她在中学的门口朝里面望了一眼,把一个给平娃的包裹放到了门卫室。
天黑之后,秀儿才到家。回到家,她便开始精心熬制瘦肉粥。本来,秀儿是极会熬粥的,但已经有许久没有做了。秀儿一边给灶膛里添加柴禾,一边给孩子喂些糖食。她还想给孩子讲些故事,可她讲不出来。
突然,秀儿的心里一阵抽搐。她立即取出海洛因,撒一撮在一根燃烧的柴头上,猛吸了两口才得以缓过神来。
孩子睁着大眼睛凑过来看热闹。秀儿一脚把他蹬得老远。
摔了跟头的孩子大哭不止,秀儿也没得心情继续熬粥。
终于,孩子在糖果的安慰下不再哭闹。
秀儿先盛了一碗粥给孩子,让他趴在一个小凳上慢慢吃。回到厨房,她把剩下的海洛因一股脑儿点燃,酣畅淋漓吸了个够。然后,给勇哥爹盛了一碗,并喂他吃下。然后,她回到厨房,给自己盛了小半碗粥,把那包老鼠药和两勺白糖一并放下去。虽然粥里加了许多白糖,但鼠药的味道依然十分浓烈。管不得那么多了,她必须一口不剩的全部喝下,并把碗洗干净,决不能让孩子沾到一丁点儿这碗里的东西。
还好,鼠药的药性并不是那么快。待秀儿把自己吃的那个碗洗刷干净,并躺到床上的时候,她的胃才开始翻腾。
孩子似乎在哭闹,勇哥似乎在呼喊她,还有,她的爸、她的妈也似乎在呼喊她,妇女主任似乎也来了,院子里似乎有十分噪杂的声音……哎呀,给平娃的信似乎忘了说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必须得调整一下房屋的方向,子午卯酉这个方位不对呀……其实,也没有关系,也用不着这么麻烦,她走了之后,勇哥爹也会被送到敬老院去,孩子会被送到外婆家去,平娃也会出门打工,这房子不再属于他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
把秀儿的智能手机送到禁毒大队并交给那个穿夹克的女人后,平娃就带着侄子风尘仆仆往秀儿的老家找去。
此文获巫山县年禁毒主题征文一等奖。
巫文弄墨系巫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巫山县作家协会主办;展示巫山本土作者及巫山籍人士文艺作品并一切关涉巫山的文艺创作,并巫山各类文艺活动。投稿邮箱:qq.转载请注明:http://www.jituant.com/djhw/8532.html